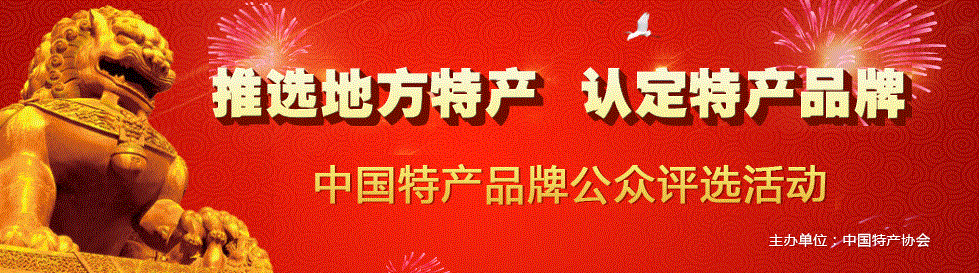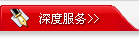安徽小岗村因为30年前的“敢为天下先”,成为闻名天下的“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这也为他们今天借助这份知名度发展旅游业积累下了资源。所以,当我们这次走进小岗村,也见识了他们红红火火在搞旅游。小岗村的旅游产品,我以为最好的还是“大包干纪念馆”。
“大包干纪念馆”的展览内容,一头一尾分别是两幅巨大的壁画,开始一幅用写实手法,表现的是30年前,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托孤”手印的故事,画面充满了彷徨和憧憬;后一幅则是形式抽象的农民画,表现30年后的今天,小岗农民的幸福生活。这番对比,折射出来的是中国农村30年间的巨大变化,而变化的关键,当然是“大包干”。
不过,中国人明白的事情,外国人未必清楚。我们参观完“大包干纪念馆”后,有个西班牙记者忽然冒出一句很生硬的中国话——“到底什么是‘大包干’啊?”我替解说员回答说:“简单点讲,‘大包干’就是三句话,‘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西班牙人显然还不太理解中国农民的概括力与幽默感,听完后就一本正经地咂摸起这句顺口溜来了。
这次和不少境外媒体的同行一起造访小岗村,有几点印象很深刻。首先是他们的认真态度;其次是他们对热点问题的把握,比如土地流转,这个问题几乎贯穿全部的采访过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理解,和我们也有一定的偏差,比如我后来看到其中一位记者的报道中,把村民的承包土地定义为“国有”,这显然是不对的。
一般来说,我们把土地权利看成一个“权利束”,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等。中国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性质,是“集体所有”,这应该是一个常识。当然,具体往下推,哪一级的“集体”所有,可能有些不同的理解,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制度,但“集体所有”而不是国家所有,这是有根本区别的。如果把“大包干”视为一种转折的符号,那么之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和之后的土地承包制度,在土地的所有权上,都是“集体所有”。
发生变化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于使用权和收益权等方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制度,实际上是把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发回给农户。“大包干”的意义是在这种既稳定又灵活的土地制度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凸显出来的。
在采访中,关友江老汉曾经多次说过一句话:“(土地承包)长期不变这个制度好啊,这样我们农民心里就踏实了。”我想问题的关键也许就在这里,“巨变”背后的深刻原因就是关老汉口中说的这个“不变”——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归于农民的不变。中国的农民要发展致富,离不开土地,通过“大包干纪念馆”里再现的历史画面,很多朋友大概能够知道,有一块真正由自己支配、收益真正归自己所得的土地,对中国的农民有多么重要;一个科学的、真正为农民所欢迎的土地制度对保障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多么重要。土地承包一方面使得农民对土地的使用和收益情况可以符合自己的现实情况,另一方面则解决了困扰国家的粮食问题。土地承包对农民来说,是面对危机的“避风港”,也是能让他们强大起来的“根据地”。因此,最近中国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且长久不变”的承诺,有的学者也将之比喻为一颗给农民的“长效定心丸”。
如何让9亿农民“心里踏实”,是中国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关于热点问题“土地流转”(流转的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小岗村的书记沈浩并不觉得是最近才有的新事物。事实上也是如此,从1988年以后,农村土地使用权的依法转让就有了法律依据。之后的有关政策法规也一直鼓励农村土地的自愿和有偿流转。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于“土地流转”问题“两个原则、三个底线”的表述是非常清晰的。对农民来说,重要的事情还是农地产权的稳定与否。一方面是承包期的“长久不变”,另一方面是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权是否能够逐步完善起来。这两个方面的大工作做好了,土地流转的规模和效率当然会上来。
这是我作为一个中国记者,就境内外同行所关心的问题,在这次采访和阅读中的一些观察。